木原音濑《渡过夜空的月之船》:表与里,光明与黑暗,求生与自毁——解密木原音濑笔下最复杂人物

*不科学不严谨不正确,仅代表个人看法
河濑史(2?-近三十)x柴冈保弘(42-48)
剧情梗概
部分抄文案:上司柴冈(42,受)以人事调动为交换条件,要求与河濑发生关系。无论如何都想进商品企划部的河濑(2?,攻),想着只要睡一次就能调入理想部门,忍着厌恶接受了柴冈的条件。但是经历如此冲击身心的交易后,人事调动的公告上并未有河濑调动的公示,反而是柴冈要调往北海道支社担任支社长,深觉受骗的河濑殴飞了欢送宴后独自回家的柴冈,使其遭遇车祸身受重伤。六年后,已当上商品企划部三课主任的河濑在上司的要求下,前往北海道负责新产品调研,与在北海道支社的柴冈再次重逢。(后面太狗血了不想写了XD
-------------------------------------------------
初读《月船》是在大约12年前,也是初入腐坑不久后首次接触木原的作品。实话说第一遍看只觉得作者对河濑被上司要求发生关系后,混乱呕吐以及一系列崩溃的心理状态描写十分写实,却并不能够理解另一边的柴冈,包括之后的几次重读,对柴冈的诸多反常之处依然难以把握。直到距离初读12年后再看这篇文,才觉得终于能稍微理解柴冈了。
柴冈是木原那么多文中当之无愧最复杂的一位,且《月船》本身也很特殊,既没有像木原其他许多作品中有双方视角的呈现,也基本没有番外(至少汉化似乎没见到?),于是正篇成了理解柴冈的唯一依据。
柴冈的复杂来源于多方面。
首先,木原对他的呈现是客观化的。《月船》是以河濑的视角去呈现柴冈,因此就很难直观地深入柴冈的内心去一窥他的所想。而在客观呈现的基础上,柴冈又是个被收着写的角色。木原对于柴冈类似软弱的情绪表达十分克制,除了短暂失明时被河濑表白夸可爱后脸红,其他时候,柴冈并不会对自己的悲惨身世报以激烈的反应,反而有种事不关己般的冷静,向河濑诉说自己与母亲的不伦过往时口气相当淡漠,甚至能笑对河濑“不正常”的反馈。
其次,柴冈的拟态即构筑了一个外在的人设形象,将真实的自我严密地包裹了起来。柴冈极度聪明严谨,这是他的拟态得以长期生效,瞒骗众人的原因。也因他的聪明,他能轻易洞察他人,不论是给予言语上的迎合满足,还是对自身异常身世不可暴露的警觉。
而上述两点也不难发现柴冈的矛盾之处,他一面拼命地遮盖自己的过往,想把和母亲的秘密直接带进坟墓;另一方面,到了不得不说的地步,他又能以全不在乎的口气将自己的不堪过往讲给河濑听。而这也是解读柴冈的难点,他是迂回、矛盾而摇摆不定的。
——内心的真相云遮雾绕,也无法直接看到人物的“痛点”,同时言语和态度上又充满违和与欺骗,解读柴冈让我不可避免地回忆起解读汤贞(《如梦令》/云住)的时候,两者都有“藏而又藏”的属性。因此,围绕角色的那些反常的蛛丝马迹就成为解读人物的关键。
完美的拟态与肮脏的家——柴冈的表与里

“拟态”是个在程度上介于社交面具与人格解离之间的词,比社交面具更密不透风,但还不到人格解离的程度。由表演和谎言构成的完美拟态,以及千方百计掩饰的真实自我构成了柴冈的表里张力。而如此表里不一的矛盾人格形成的背后原因在于柴冈能敏锐地洞察社会奖励其自身定义的“普通/正常”而惩罚排斥“异常”的暴力逻辑。
柴冈在职场构建了一个完美无缺的上司形象,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他基于对人的了解以及对社交距离精准把握,而敷衍众人的谎言。可以试想一下,若当初去他家寄宿的并非见识过他另一面的河濑,而只是其他同事,那么母亲去世后,自己不擅整理的说辞结合他在人前一贯的良好形象,垃圾屋极有可能被粉饰为“完美上司也有弱点”的反差萌版本流传到职场,反而在无懈可击之余给他增添了人情味,从而转移他人对异常的垃圾屋本身的关注。
但几篇文解读下来,私域读心法(x告诉我们,私域确确实实是人内在毋庸置疑的延伸,极为直观诚实地反应着屋主的状态。换句话说,“不擅整理”可以是一句托辞,但混乱邋遢的房间却也是种客观真相,对应着柴冈一片混乱荒芜、难以重建和恢复的内心。
柴冈的聪明让他从小就能意识到在普通的范畴里,单亲家庭较之父母双全的家庭要弱势一些,为了不惹人注目,他“在学校表现得很老实”,但私生子身份的自卑和不完整家庭的缺失感已经埋下了种子。未及结束学生时代,母亲在他15岁时“不H就去死”的强迫进一步将柴冈拉向异常的深渊,不但没来得及向他憧憬的普通人生靠近一步,反而距离越拉越远。而当柴冈终于决定“将自己的人生献给母亲”,且以夫妇身份虚构出一重“正常”时,母亲遗书中将他作为父亲替身的事实不但否定了他努力构建出的“正常”的假象,更是残酷地抹消了他的存在价值。
从中可以看到,柴冈一路成长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两个本能:
一个是让自己不成为异类而顺利嵌入集体的社会性本能(单亲家庭—表现低调),以及当这一本能越来越无法被满足后,拼命遮掩补救、自我合理化的求生本能(母亲的性胁迫—无法拒绝—回应母亲扭曲的爱情)。
不论是否病态,柴冈人生中最复杂深厚的情感联结都是与母亲缔结的——通过压抑和欺骗自我的方式。然而母亲在掠夺完柴冈的生命价值后,又通过自杀轻率地抛弃和背叛了他。对于柴冈而言,母亲的做法无疑摧枯拉朽般地毁灭了他赖以生存的价值基础,也否定了他的感情或努力,将他漫长的二十多年自我奉献的人生置于无物;同时她也用死亡给柴冈留下了一个无可诘问也无处复仇,无法修补也无可挽救的永恒的“异常”的黑洞。
柴冈的拟态在母亲死前若是一种掩饰异常、试图企及普通人生的努力,那么在母亲死后,拟态与真实自我的距离进一步拉大。柴冈利用拟态(投入工作)逃避灵魂深处“我”之为“我”价值何在的自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母亲否定的微弱抵抗。人的求生本能驱使,他未必不想从其他事物中寻找摆脱母亲阴影的方法——拟态的产生应该说就是柴冈无法由衷将乱伦合理化而自我无意识进行平衡和调节的权宜之策。然而他在职场表现出的完美恰恰与他对自身异常的体认互为镜像,母亲的阴影和影响过于漫长强大,因此柴冈几番自救的尝试,收效甚微。
夜盲症与失明——无法被彻底压抑的真实自我的反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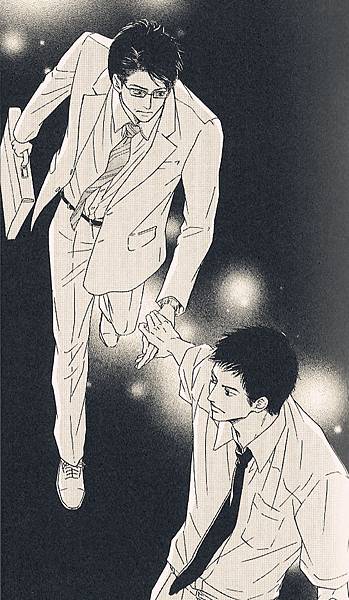
黑暗对柴冈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涵义。尽管他说过“人的内心没有黑暗”,但那仅是他的自我欺骗。柴冈从小就害怕黑暗,少年时第一次被母亲强迫也发生在夜晚;看到上吊自杀的母亲是在没开灯的屋内;将真实的自我不断地遮蔽(在暗中);夜晚睡觉从不关灯……黑暗与他的诸多冲击性经历相连,是对柴冈而言十分具体也颇有寓意的符号。
柴冈虽在与河濑讲起自己与母亲的不堪过往时是一副相当漫不经心的口吻,但他的淡漠并不意味着母亲曾加诸于柴冈的暴力和创伤也就此风轻云淡。木原在文中通过人物与情节的对照,隐晦地暗示着柴冈所受到的创伤以及他当时的心境。
故事开头柴冈以调职要挟河濑发生关系,柴冈以“接纳”的形式强暴了河濑,这一情节,与柴冈被母亲强迫发生关系形成对位——相近的年龄差、都是不那样做就可能会强烈后悔的情形、柴冈也是以插入方的身份被母亲强暴,抛开身体上可悲的快感,他们都经历了主体性被侵犯的过程。而河濑误会自己被玩弄欺骗也与柴冈被母亲的自杀抛弃和背叛对应。
木原以“健全的河濑”对于这两件事的一系列反应:恶心、呕吐、崩溃、羞愧、愤怒、后悔等激烈情绪,以及反应在身体上灰败消瘦的病容病态来表达强暴和“欺骗”给他留下的创伤。遥遥指向15岁的柴冈以及41岁的柴冈所经历的冲击的能量烈度。
其次则是河濑照护暂时失明的柴冈期间,从无法摆脱男人的焦头烂额几欲崩溃,到救回被赶出去又意图寻死的男人后,决心“将身体借给他”的妥协,到对柴冈产生无法割舍的感情这一过程,与柴冈将和母亲的关系自我合理化的过程也相类似。
柴冈无法摆脱母亲,更确切地说,是无法承担一旦离开而导致母亲真的死去的良心谴责,他唯有将“自己的人生献给母亲”。只不过柴冈的自我合理化(“自己只是娶了一个名叫母亲的妻子”)与他洞察并服从社会奖惩规则(乱伦是异常的)这两点本质上无法自洽,换句话说,柴冈其实无法由衷地接受和母亲的关系,于是他只能将无法自洽的事实往暗处藏,并建构出一个表面完美的拟态作为逃避面对真实的方式。
由此,柴冈的表里也形成了多重复杂的张力关系——
【看见—现实—明处—拟态—虚假】 VS 【看不见—内心—暗处—自我—真实】
但当那些无可逃避的时刻到来,比如母亲遗书中的真相恒久地否定他并宣判他的异常,以及河濑阻止他在父亲的忌日自杀去陪伴母亲,从而无法再自我欺骗时,柴冈失明了。
柴冈在故事开头,因为黑暗而无法前进的时候说,“看着黑暗,总觉得不知何时自己也会被吞进去似的,就变得害怕起来。”
柴冈的失明不是身体的器质性病变,而是于他而言十分形象的神经症:在巨大的情感事件冲击下,那个被他封印在暗处的令他恐惧的真实自我开始反扑,以吞没光明的方式提醒自己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柴冈的夜盲症也就耐人寻味了,它似乎并不纯粹是躯体老化后的症状,更像是柴冈那个无法被彻底压抑的“异常”自我时常漫溢出来,提醒他无法摆脱的过往。
柴冈的矛盾——执意求死又渴望拯救

柴冈有求生的本能,却又频频尝试自毁,生死若在两端,那么柴冈在趋于生又投向死的两条路上不断往返,就算到故事的最后,柴冈涉入海中去触碰海面上月亮的倒影形成的月之船(自杀)也是为了被拯救。
上面两点其实已经写到了柴冈在生死间往返挣扎的动因何在:即人的求生本能与人的存在价值被否定后产生的自毁倾向之间的角力。只是当柴冈将河濑也牵扯进来后,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柴冈毫无疑问受到河濑的强烈吸引,对方的普通跟健全是他一直憧憬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在河濑十分自然地牵起黑暗中踟蹰不前的他的手,将他带往光亮处,拯救的意味不言而喻。但面对这样一个可能的拯救者,柴冈的态度却同样是摇摆的。他既渴望被拯救,又不信真的会被救。
柴冈没有忍住向河濑出手,提出睡一次的交易。他未尝不好奇当健全如河濑遭遇和当年的他类似的处境时会怎样。6年后再重逢,柴冈将可能自杀的打算告知河濑,并在他面前一次次试图自杀——固然他确实有自杀的真心,有时也并不确知河濑在附近——但那同样也像是一种拴着安全绳的“自杀表演”,是柴冈不厌其烦地在测试河濑是否真的会救他。
但当河濑真的一次次救他,他又无法相信,同时也恐惧一旦与河濑建立情感联结,他无法承受再次失去的后果。因为柴冈对真实自我的认知,从单亲家庭的尚算普通,到被母亲强迫后的异常再到被母亲背叛否定后的无价值,是一步步无可挽回地走向“烂到不能再烂”的人生的过程,这也注定了他永远无法摆脱自卑,真正地肯定自己。
他可以在第二次失明时忠于欲望,频繁地向河濑索求——因为欲望是被他遮掩起来的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但却在被河濑表白喜欢这个真实的、不那么好的他时,脸红颤抖地蜷缩成一团。可爱之余,这确确实实是他极度自卑的表现,他不信河濑会永远救他乃至于不断地测试对方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不认为不堪的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或者会被什么人真正需要,当河濑的新鲜感过去,他就会被再次抛弃。
柴冈复明的契机也颇有意思,当他所有的秘密被河濑洞悉并被河濑告白,柴冈的自卑让他涌起强烈的窘迫和不安——他可以身体赤裸,却无法忍受内心的赤裸,柴冈急迫地想要躲藏的需求也令他结束了为时几个月的失明状态,飞速逃回北海道的家并再次用刻薄毒舌的拟态来自我武装,以重构自身的安全感。
另一方面,柴冈的父亲在柴冈母亲14岁时令她怀孕、15岁生下柴冈;而柴冈又在15岁时被母亲强迫;并且他自己与河濑的关系又隐隐像是当年母亲与他的关系,不幸在相似的巧合中如诅咒般地传递下来,柴冈看河濑,不知是否会有一种看他自己当年的感觉。而作为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柴冈或许并不愿意河濑成为另一个自己。但不论柴冈是否愿意,河濑都已经进入了在柴冈眼里诅咒般的关系中,不论他自杀与否,柴冈都成为了当年他母亲的角色。
故事结束在河濑打碎海面上虚幻的“月之船”,稳稳地拉住柴冈,将他又一次带离死亡。与柴冈所担心的诅咒的传递稍许不同的是,河濑是“普通”且健全的,他似乎可以成为一个结束诅咒的有力变量,但也或许即便是河濑,依然敌不过柴冈母亲留下的阴影而最终无法挽留住柴冈。
两人的未来会如何,这一问题的答案被悬置于同样摇摆未定的可能性中。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 article.title }}
{{ article.title }}